返古歸真在神權政治中為何必然成為權力鬥爭,而非真理回歸?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返古歸真在神權政治中為何必然成為權力鬥爭,而非真理回歸?
神權統治的根本前提,在於「神的旨意是確定的,而且可以被某個具體的人或群體正確掌握」。一旦這個前提成立,政治秩序便獲得了一種世俗權力無法比擬的正當性來源:服從不再只是對人,而是對神;反對不再只是政治異議,而是宗教背叛。因此,在神權體制中,最關鍵的不是制度設計,而是誰能合法地壟斷對神意的詮釋權。
在伊斯蘭的創立階段,這個問題並不存在。穆罕默德既是先知、宗教權威,也是政治與軍事領袖。他的權威不是制度性的,而是人格性、啟示性的。他之所以能統合宗教與政治,不是因為他設計了一套可繼承的神權制度,而是因為他被視為神意的直接傳遞者。問題恰恰在於:這樣的權威無法被制度化複製。
穆罕默德過世後,伊斯蘭世界立即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真空:如果神的最後一位先知已經離世,那麼誰有資格代表神?這不是單純的行政接班問題,而是一個神學—政治的根本斷裂點。哈里發制度(Caliphate)的誕生,本質上是一種補救性安排:不是再宣稱有人能直接聽見神,而是宣稱有人能「繼承」先知在社群中的地位。然而,「繼承」本身就是一個曖昧而危險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為血統、也可以是品德、學識、或政治能力。
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裂,正是在這個曖昧點上爆發。什葉派主張領袖必須來自先知的家族,因為只有血統的連續性,才能維持神聖權威的純度;遜尼派則傾向於承認社群共識與政治現實,認為領袖的合法性來自烏瑪(穆斯林共同體)的承認。這場分裂不是神學細節的爭執,而是對「神意如何在歷史中延續」的根本分歧。
然而,這並沒有結束問題,反而使問題層層加深。什葉派內部隨後又出現五伊瑪目派、七伊瑪目派、十二伊瑪目派的分裂,顯示即便訴諸血統與神聖家族,也無法避免「誰才是真正繼承者」的爭議。十二伊瑪目派最終訴諸「隱遁的伊瑪目」,某種程度上正是對這個困局的神學性凍結:既然無法確定誰有資格統治,那麼真正的合法統治者暫時不在世上。
遜尼世界看似避免了血統神權的困境,卻走向另一條同樣無解的道路:返古歸真競賽。既然沒有一個被普遍承認的神聖繼承者,那麼合法性的來源只能退回到「誰最像穆罕默德時代的伊斯蘭」。於是,瓦哈比派、塔利班、伊斯蘭國等運動,都不約而同地宣稱自己最忠於最初的烏瑪、最純粹地實踐先知的教導。
問題在於,這場比賽從一開始就沒有裁判。
穆罕默德時期的伊斯蘭社群究竟如何處理日常生活、政治衝突與道德抉擇,我們所能依賴的資料極其有限。古蘭經並不是一本全面的法律或政治手冊;聖訓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口述、編纂與篩選過程,本身就深受後來政治與教派立場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即便文本存在,詮釋永遠無法被唯一化。不同教派、不同法學傳統,對同一段經文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因此,「返古歸真」在現實中並不是回到一個可驗證的歷史原點,而是把當代的權力主張投射到一個模糊的神聖過去。誰能動員更多武力、資源與信徒,誰就能暫時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伊斯蘭」。這不是神學競賽,而是政治鬥爭披上神聖語言的結果。
這種現象並非伊斯蘭獨有。16 世紀的新教宗教改革,同樣高舉「返古歸真」的旗幟。路德、加爾文等改革者批評羅馬大公教會積累了大量初代教會並不存在的教義、儀式與權威結構,主張回到《聖經》與使徒時代的純正信仰。然而,宗教改革並沒有帶來一個單一、被普遍承認的「原始基督教」,反而迅速導向教派分裂與神學多元。
這一點極為關鍵:返古歸真不是回到原點,而是打開分裂的起點。
因為一旦最高權威從「現存制度」轉移到「被詮釋的過去」,那麼誰掌握詮釋權,誰就掌握正統性。天主教以教會傳統與教宗權威回應新教,新教內部則迅速分化出路德宗、改革宗、再洗禮派,乃至後來無數教派。每一方都可以宣稱自己才是最忠於初代教會者,而沒有一個超越歷史與權力的仲裁者。
由此可見,神權政治最深層的矛盾在於:它需要一個絕對的神意來源,卻只能依賴相對的人類詮釋。只要神不再直接說話,神權就必然轉化為人權;只要轉化為人權,它就不可避免地捲入權力競爭、暴力與政治計算。
因此,返古歸真並不是神權政治的解方,而是它的症狀。當現存權威無法自我正當化時,才會不斷呼喚一個「更純粹的過去」。而那個過去越模糊,越容易被動員為權力工具。


.webp)

.webp)

.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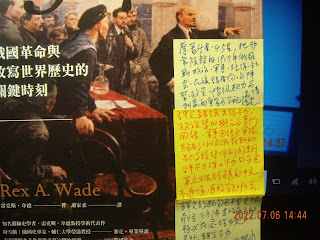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