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同一波神權—威權失效(阿拉伯之春),會導向三種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且為什麼第三種如此罕見、脆弱、幾近偶然?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為什麼同一波神權—威權失效(阿拉伯之春),會導向三種完全不同的結果,而且為什麼第三種如此罕見、脆弱、幾近偶然?

下面以三個案例為主軸,把它們提升為一個可重複適用的政治理論說明。
阿拉伯之春本質上不是一場「民主革命」,而是一場合法性全面破產的集體爆發。不論是世俗威權還是宗教威權,人民拒絕的並不是某一個政策,而是整個統治敘事:你不再代表正義、秩序或未來。問題從一開始就不是「誰上台」,而是:在舊的合法性死亡之後,什麼力量有能力、也有意願接住這個真空。
一、埃及:第一種終局──軍事強人上台,不是反革命,而是「秩序替代」
埃及的路徑,常被描述為「民主失敗」或「革命被偷走」,但這其實低估了問題的深度。真正的關鍵在於:埃及社會沒有任何一個非軍事組織,能同時滿足三個條件:
第一,能在全國範圍內動員;
第二,能被視為避免內戰的力量;
第三,能即刻接管國家機器。
穆斯林兄弟會能動員,但它本身就是高度爭議性的宗教政治力量;
自由派與青年運動有象徵性,卻沒有組織密度;
國家行政體系與經濟命脈,則始終掌握在軍方手中。
在這種結構下,軍事強人不是「奪權者」,而是唯一被多數人視為「不會讓國家立刻崩解」的選項。人民不是熱愛軍事統治,而是恐懼無政府狀態。這正是前面反覆指出的主題:逃避自由的集體選擇。
因此,埃及的第一種終局不是例外,而是在高度軍事化國家中最具機率的結果。神權與威權失效後,軍隊不需要神話,只需要秩序恐懼。
二、敘利亞:第二種終局──內戰,不是革命升級,而是暴力壟斷破裂
敘利亞的情況則代表了另一種結構性失敗:當沒有任何一方能重新建立暴力壟斷時,國家就不再是單一行為者。
阿薩德政權的神話在阿拉伯之春中迅速崩解,但與埃及不同的是,敘利亞軍隊本身就不是一個「國家軍隊」,而是一個高度宗派化、家族化的安全網絡。當鎮壓開始失效,裂解幾乎是必然的。
這裡必須強調一點:敘利亞陷入內戰,不是因為反對派太激進,而是因為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替代中央暴力壟斷。一旦這個壟斷破裂,局勢就不再由政治決定,而是由武器、資源、外部勢力共同塑造。
此時,「革命」這個詞本身已經失效,取而代之的是:
軍閥化、代理戰爭、宗派動員、難民化社會。
這是一種主權解體型終局,代價最高,復原最難。內戰從2011年開始,到2024年才結束。
三、突尼西亞:第三種終局──談判式轉型,為什麼如此罕見
突尼西亞之所以特殊,不在於人民比較「民主」,而在於它同時滿足了三個極少同時出現的條件。
第一,軍隊規模小、政治化程度低,無力也無意接管國家;
第二,伊斯蘭政黨(如安那達黨)願意接受退讓,而非壟斷真理;
第三,世俗菁英、工會與公民社會仍保有組織連續性。
換言之,突尼西亞不是因為「理想主義成功」,而是因為沒有任何一方有能力把全部權力吃下來。在這種相互制衡卻又彼此恐懼的結構下,談判反而成為理性選項。
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第三種終局如此脆弱:
它不是建立在壓倒性的力量之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克制的疲憊感之上。
一旦經濟惡化、外部壓力增加,這種脆弱平衡就很容易倒退。
四、三種終局背後的共同邏輯
把這三個案例放在一起,其實已經指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
阿拉伯之春不是選擇了不同的道路,
而是被各自的國家結構推向不同的結局。
不是「人民想要什麼」,
而是「誰能在合法性死亡後,接住秩序」。
五、一句總結,作為這一整條論述的理論核心
當神權與威權同時失效,
政治的未來不取決於理念的高尚,
而取決於:
是誰能在混亂邊緣,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
並且願意不把那份秩序神聖化。
埃及,有秩序,無自由;
敘利亞,無秩序,無國家;
突尼西亞,短暫地,嘗試在沒有神話的情況下治理自己。
而這,也正好回應了核心問題:
人民是否能承受沒有終極保證的自由?
歷史給出的答案是:
極少數可以,而且需要非常特殊的條件。



.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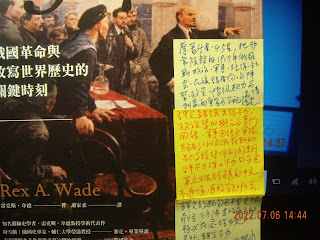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