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後:為何推翻神權並不保證自由得以存活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自由之後:為何推翻神權並不保證自由得以存在
自由之後:為何推翻神權並不保證自由得以存活
——論「逃避自由」、世俗強人與國族主義的結構性回歸風險
一、問題的真正嚴重性:這不是過渡期的枝節問題,而是文明心理的斷層
「推翻伊朗神權政權之後,人民會不會因承擔不了自由的責任,而逃避自由,轉而擁抱世俗強人與國族主義?」
這個問題之所以尖銳,不在於它是否政治不正確,而在於它觸及了一個自由主義長期迴避的核心事實:
自由不是人類的自然狀態,而是高度不自然、反直覺、反心理舒適的制度安排。
神權政治之所以能長期存在,不只是因為暴力或洗腦,而是因為它成功回應了人類對「意義確定性」的深層需求。當這種體制被推翻時,隨之而來的,並不只是政治解放,而是意義結構的全面崩塌。而人類對這種崩塌的耐受力,遠比自由派想像得低。
二、神權政權真正留下的遺產:不是信仰,而是人格結構
長期生活在神權體制下的人民,並不是單純「被壓迫者」,而是在不知不覺中被塑造成一種特定的人格結構。
這種人格結構具有幾個深刻特徵:
它習慣於外在權威給出終極答案;
它傾向將責任向上轉移,而非向內承擔;
它將服從理解為道德安全,而將選擇視為風險。
在這種結構中,「正確」比「自由」重要,「被引導」比「自行判斷」安全。
神權政權的可怕之處,恰恰在於它讓這種人格結構看起來合理、甚至高尚。
因此,當神權崩解,自由並不是以「解放」的形式出現,而往往以「被遺棄」的形式降臨。
人民第一次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神、沒有革命、沒有歷史使命,那錯誤算誰的?
三、自由的心理代價:為何「沒有人替我負責」比壓迫更可怕
自由政治的核心要求,不是投票,也不是言論,而是承擔後果的能力。
這意味著三件極其沉重的事情:
第一,錯誤不再能歸咎於權威;
第二,失敗不再能被解釋為「必要的犧牲」;
第三,苦難可能真的「沒有意義」。
這正是佛洛姆 (Erich Fromm) 所謂「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的心理根源。
人類並非天生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心理可承受性。當自由意味著長期不確定、道德孤獨與存在焦慮時,人類極容易得出一個結論:
與其承擔自由的重量,不如交出自由,換取確定性。
這不是道德墮落,而是心理防衛。
四、為何神權崩解後,世俗強人特別具有吸引力
世俗強人並不是神權的反面,而是它的心理繼承者。
強人政治之所以在後神權社會中迅速崛起,原因不在於它更自由,而在於它成功保留了三個神權時代的關鍵功能:
它提供簡單因果:
——問題不是結構性的,而是「有人在破壞」。
它提供集體尊嚴:
——不是你失敗了,是我們被羞辱了。
它提供責任轉移:
——把決定交給我,我替你扛。
對一個剛失去神學保證的社會而言,這種敘事幾乎是心理止痛藥。
民族主義在此扮演的角色,正是「世俗化的救贖神話」:
它不需要上帝,卻同樣承諾歷史站在我們這邊。
五、歷史的冷酷證詞:自由並不自動勝出
如果我們誠實看待歷史,就必須承認:
神權或極權崩解之後,自由失敗的案例,遠多於成功的案例。
不是因為人民不值得自由,而是因為自由需要的條件,遠比「推翻暴政」苛刻。
當經濟崩潰、秩序失控、外部威脅並存時,抽象的自由權利往往輸給具體的安全承諾。
在這種情況下,強人並不是被誤選的,而是被理性選擇的。
這一點對伊朗尤其殘酷。
伊朗同時具備三個高度危險條件:
深層國家(革命衛隊);
強烈的歷史民族敘事;
長期的外部制裁與敵對。
這正是孕育「世俗威權+國族動員」的完美溫床。
六、那是否意味著悲觀宿命?不完全是,但代價極高
即便如此,結論仍不能簡化為「伊朗必然走向強人政治」。
歷史同樣顯示,某些社會確實學會了承受自由,但條件極為苛刻。
關鍵不在於文化優越,而在於是否做到三件事:
第一,自由被去神聖化。
它不被描述為救贖,而被描述為不完美的管理方式。
第二,政治被降級。
沒有「偉大復興」,只有笨拙協調。
第三,失敗被正常化。
錯誤不是背叛,而是制度的一部分。
這樣的自由,不激動人心,卻相對穩定。
七、結論:真正的危險不是自由,而是把自由當成答案
所以,回到原本問題,最誠實的回答是:
是的,人民完全可能因承受不了自由的重量,而逃避自由,轉向世俗強人與國族主義。
但這不是因為人民不成熟,而是因為:
任何被期待填補意義真空的政治制度,都終將被重新神聖化,並再次壓迫人。
自由若被當成「終極解答」,
它就會立刻失敗。
真正可承受的自由,反而是一種拒絕承諾救贖的政治狀態。
收尾一句(不安慰,也不煽情)
自由的最大考驗,不是推翻暴政的那一刻,
而是在人們發現:
沒有任何東西會替我們保證歷史正確之後,
我們是否仍願意彼此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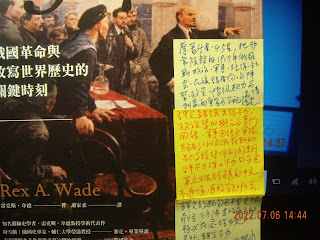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