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神權無法再令人信服時,世俗政治是否真的比較安全?還是只是換了一套新的「絕對性」來填補同一個真空?
【丁連財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評論】當神權無法再令人信服時,世俗政治是否真的比較安全?還是只是換了一套新的「絕對性」來填補同一個真空?
這是一個直指現代政治核心的問題,而且答案並不安慰人。**神權的崩解,並不自動帶來溫和、理性與安全的世俗政治;它更常帶來的是「絕對性的轉移」,而非「絕對性的消失」。**換句話說,真空很少保持真空。
當神權仍然有效時,政治秩序至少有一個清晰的終極來源:神的旨意。這個來源可以被質疑、被濫用、被暴力維持,但它在心理與象徵層面上,提供了一種「超越歷史」的正當性。一旦神權瓦解,並不是所有社會都能立即接受一個冷靜的結論──世界沒有終極保證,政治只能是有限理性的安排。多數社會首先面對的,其實是失序與焦慮。
因為神權的功能,不只是統治工具,它還承擔了三個深層角色:
第一,提供終極意義;
第二,裁決不可爭論的問題;
第三,替人承擔不確定性的重量。
當這三個角色突然消失,人們並不是立刻變得成熟,而是暴露於一種心理與政治的裸露狀態之中。
從歷史經驗看,神權崩解後的世俗政治,大致會走向三條不同但彼此可轉換的路徑。
第一條路徑,是有限性的世俗政治。
這是最理想、但也是最困難的一條。它承認沒有任何制度、理念或領袖能代表終極真理;政治只是用來管理衝突、降低暴力、延緩災難的工具。在這條路徑中,法律是可修正的,權力是可輪替的,政策是可錯誤的。它的穩定性不是來自信仰,而是來自程序、妥協與時間。
這樣的世俗政治確實比較安全,但它對人民的要求極高:
人民必須能承受沒有神、沒有歷史必然性、沒有命定領袖的世界。
也就是先前問過的問題──人民是否能承受「沒有終極保證的自由」?
現實是:很多社會,不能。
於是,第二條路徑出現了:世俗化的絕對性替代物。
當神不再令人信服,政治往往不會變得謙卑,而是轉向新的「世俗神祇」。這些替代物表面上是理性的、歷史的、科學的或民族的,但在結構上,它們與神權極為相似,因為它們同樣聲稱:
「我們掌握了不可質疑的終極原理。」
這些替代性的絕對性包括但不限於:
民族(Nation)
人民(The People)
歷史必然性(History)
革命正統(Revolution)
安全與秩序(Security)
它們的共同特徵是:
一旦被質疑,反對者就不再只是政見不同,而是被指控為「背叛民族」、「違逆歷史」、「破壞安全」、「站在錯誤的一邊」。
這正是20世紀極權政治的核心邏輯。
納粹不是神權國家,但「民族—元首—歷史使命」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準宗教體系;
史達林主義否定上帝,卻以「歷史法則」取而代之;
毛主義摧毀宗教,卻把革命正統神聖化。
在這些體制中,神死了,但神的位置被更粗暴、更不可反駁的東西佔據了。
第三條路徑,是與伊朗問題直接相關的:神權崩解後的「強人世俗化」。
當神權不再被相信,但社會又無法承受多元、不確定與責任分散時,人們往往會選擇一個看似世俗、實則功能等同於神的存在──強人。
強人不需要宣稱自己是神的代理人,他只需要承諾三件事:
我能讓混亂停止;
我能替你做決定;
我能讓你不必再思考。
這正是威瑪德國的經驗,也是一再重演的現代劇本。
人民不是被剝奪自由,而是主動交出自由,因為自由的心理成本太高。
因此,回到問題本身:
當神權無法再令人信服時,世俗政治是否真的比較安全?
答案是:
只有在它拒絕成為新的絕對性時,才比較安全。
而這恰恰是最難做到的事。
因為世俗政治若要真正安全,必須同時接受三個極不討喜的前提:
第一,政治沒有終極答案;
第二,制度會失敗,人會犯錯;
第三,沒有人、沒有理念,能替人民免除承擔後果的責任。
這不是英雄敘事,而是一種「去神話化」的政治成熟。
最後,用一句話收束這整個問題的核心:
神權的終結,不保證自由;
它只創造了一個空位。
那個空位,要嘛被制度的有限理性填補,
要嘛被新的世俗神話佔據。
真正的危險,不在於有沒有神,
而在於人是否仍然渴望一個不可質疑的東西,來替自己承擔自由的重量。

.webp)
.webp)

.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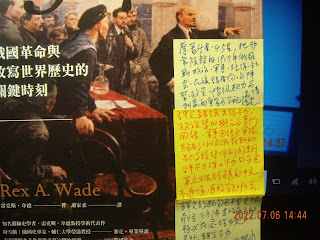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